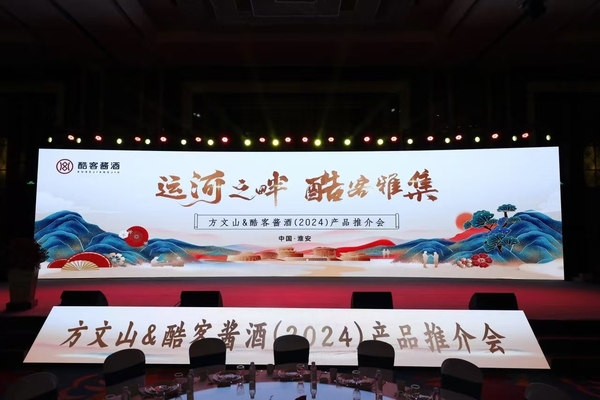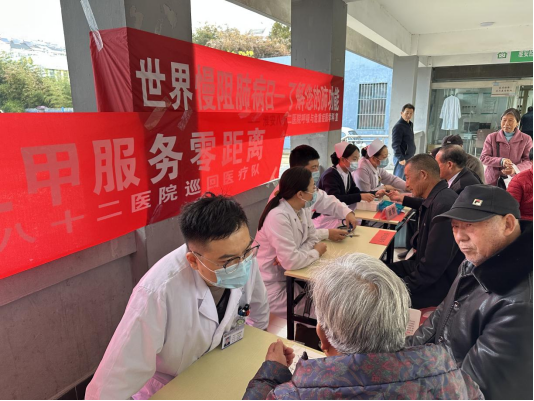■蒋长林
尽管父亲生命力非常坚强,与心肺等疾病抗争了十多年,终究没能战胜“新冠”这个恶魔,于2022年12月31日永远离开了我们,享年92岁。
在渔沟老家,知道父亲大名的人不多,但提起“老实头铁匠”,乡邻们就都知道是谁了。
父亲小时候被过继给他伯父。虽然家庭条件也不好,但有两对父母的“宠爱”与管束,倒也没吃太多的苦,加上长相俊朗,乍看还不像农村孩子呢。不过也因管教严格,从此打上老实听话的本色。
我爷爷是较有远见的农民,克服了许多困难,将父亲送入渔沟完小读书。不负家长希望,父亲一入学就乖巧好学,深受老师喜爱。后来他教我们识字也有一个独特方法:将废报纸中间剪个洞,下面的纸上则写上字,像放幻灯片一样让我们认。认对了就奖励一块山芋干或几粒炒黄豆。
父亲原本可以走上求学“食禄”之路的,小学没毕业,兵灾降临。我奶奶怕他被抓壮丁,硬是让他辍学,送去浙江学铁匠手艺。从此文弱瘦小的父亲走上了坎坷艰难的求生之路。
在十来个学徒中,父亲年龄最小,个头最小,力气也最小,根本挥不动大锤;加上师父家孩子多,牲口多,土地也较多,学徒期间,父亲更多的是割草喂猪,砍柴放牛,带娃打杂,基本上没学到真功夫,徒有“蒋铁匠”之名。难怪后来每当农忙季节或家里铁制农具坏了,我们就嚷嚷让他打一组新的,他就“嘿嘿”笑两声应付过去。至于被当长工使唤,师母刻薄寡恩,师兄弟们顺势戏耍他的事,我们也是从母亲嘴里掏出来的。
爷爷奶奶知道后,毅然让父亲回来,让他跟着他二哥(我二伯父)去贩卖黄泥盆水缸猪食槽等农家用品。这可更是吃辛受苦的强体力活。一帮人每人推着码着又高又重的货物的独轮车,走南闯北,风餐露宿,一出去就是十天半月甚至近一个月才回来。这需要多大的体能耐受和坚韧意志哦!而这时的父亲也才不到20岁,是个发育不良、一米五几的瘦弱青年呀。
与那时的大多数同龄人一样,父亲是由爷爷奶奶决定在他7岁时结娃娃亲的。许是老天对善良本分、老实顺逆父亲的馈赠吧,21岁那年,他如愿迎娶了倾慕已久的郭家大美女,也就是我的母亲。大父亲2岁的母亲不仅人美丽,而且一手女工十分出色,男人干的活大多亦能拿下。更重要的是,她在家是长女,从小养成了干练、果敢、不服输、不吃硬的性格,而这正好是木讷少言、内敛懦弱父亲性格的补充。正是刚强的母亲,艰难撑起了我们的家,虽然经常过着缺吃少穿的生活,但苦中有乐,累中有甜。而他俩互补的性格也养就了我们姐弟(兄妹)五人本分坦诚、耐劳坚韧、律己利人的良好品行。
有了贤惠勤劳、几乎全能的母亲精心操持着家,父亲可以专心在外做点苦力活了。虽然收入微薄,但终归有点家用补贴,隔三岔五回来都能从城里或集镇提几根油条,逢年过节还能拎二三斤五花肉或半个猪头回来,两个姐姐有时还能得件新衣裳呢。
一段时间,农民做生意也属于“资本主义尾巴”,是要被割掉的。胆小听话的父亲一听大队生产队干部宣传,就丢掉生意,回家一心务农了。由于从书房出来就去学手艺“跑单帮”,加上瘦小力弱,很多农活他根本拿不下来。庄上有几个龌龊鬼经常捉弄他:上河工将父亲推的土车堆成小山似的;与父亲抬泥筐故意将重的一端抹到父亲那头;粮食入库也将父亲扛的笆斗装得满满的......看到父亲吃力痛苦状,他们就开心乐怀起来。
见如此老实本分、又写一手好字的父亲,宅心仁厚的老队长顶住压力,“力荐”父亲当副队长。守规认真的父亲办起事来几近迂腐,执行领导指示绝不走样。记工分、分粮油的账本弄得工工整整、清清白白。在父亲前任那多讨几个工分、多分几斤粮食的一些“里手人”被父亲发现取消,气得指桑骂槐。父亲到公社和大队办事,上传下达等活计皆有板有眼、有质有效。不到半年,大队干部和生产队大多数农户都夸老队长有眼光,配了一个正派公道、做事认真的“好队副”。
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基本上就是一月左右到每个生产队放一次电影(以八个样板戏和三战【地道战,地雷战,南征北战】为主),或听《杨家将》等评书。或许我们家离队房最近,更多原因应是对老实厚道父亲和利索能干母亲的信任,放映员和说书的饭总在我们家做。尽管也就是大白菜豆腐粉丝够吃而已,但毕竟有些猪油(偶尔也有点肥多瘦少的肉片或油渣),满院溢香。我被馋得直流口水,父亲也决然不让我上桌的。
记忆深刻的是父亲接手生产队十来头牛的喂养任务,他就一年四季全与牛住在一起了。春秋两季还好,冬天西北风直灌,他只睡在麦草铺垫的光席上,只有一张薄棉被;夏天则蚊蝇横飞,加上牛粪尿牛骚味,熏得人直作呕。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,父亲皆坚持每夜两三点钟为牛们添加饲料,及时清理牛粪尿。白天则将社员上交的饲料草中带刺的逐一挑去,与母亲将草料铡得碎碎的,用耙子、扫把等为耕牛梳理皮毛,去虱消痒,还定期为它们洗身,填喂精饲料。不到3个月,原来骨瘦如柴、精神萎靡的牛们被他调养得膘肥体壮,“神采奕弈”,干起活来劲头倍足。
父亲对牛的疼护几近不可理喻。经过磨练,他也已成为扶犁好手。每次牵牛下地,他皆哼着小曲给牛听,耕了半小时左右,就让牛歇十来分钟。即使挥鞭,也是作吓唬状,很少鞭直接打的。养了牛后,更是呵护有加。每当有人来牵牛下地,他都要按自己做法反复叮嘱他们要爱护好它们,还告诉他们每条牛的“性格脾气”。一位姓胡的耕地好手,一次为了抢时间回家有事,猛赶进度耕田,被他牵去的牛被打得遍体鳞伤。从没在外人面前发过脾气的父亲火冒三丈,还口出粗话,与姓胡的大吵起来。比父亲高半个头、五大三粗、平时横三竖四的他被我父亲这架势吓得落荒而逃。
一头叫“大角牛”的老黄牛非常温顺耐苦,是每个耕田者争要的。因年老体衰而亡,父亲守在它身边好久好久。按“惯例”杀掉后每户都要分二三斤肉的。父亲呆呆望着我们吃着煮熟的牛肉喃喃而语,多好的牛啊!这下不受罪了!
和那时的大多数农家一样,我们家也是低矮土墙茅草屋。每到雨季,不是墙倒塌就是屋顶漏,每当此时,父亲就不顾一天的劳累,晚饭后就把从远处推回来的泥土,用碎麦草搅拌成硬糊状,将倒塌的墙一块一块砌起来。有时我都睡了一觉,还见他就着昏暗的煤油灯干着;又利用午饭后时间选筛麦秸草,待晴好天请庄邻将漏雨的屋顶修补好。
有些年,父亲因生两个女孩(我大姐二姐)而被一些村邻讥笑,甚至被生了三个儿子的邻居欺凌。刚强的母亲强势以对,有理必争;父亲则淡然一笑,不以生两个女娃而自卑,并决定认真培养好两个姐姐。谁知二姐6岁时我出生了,父母爱的天平一下子倾斜了。为了培养我,两个姐姐连学都没上。我读高中上大学时,两个姐姐分别出嫁,又硬生生将学习非常好、小学还没毕业的大妹摘下来当强劳力使用。因长时间劳作过度,大妹落下一身病痛。每当我想起这些,心中对她们的愧疚之情就油然而生。
我小时候体弱多病,差点一命归西。父亲要么推着独轮车,要么拉着借来的平板车,用被子裹着我到处求医。匆匆而沉重的步履分明映出他的焦虑与无助。或许老天有眼,或许我命不该绝。在从外地返乡工作的纪医生(按辈份我叫七爷)调治下,我渐渐好了起来。
因为父母30多岁才有了我,又是唯一男孩,且是从鬼门关拉回来的,我侍宠而骄。在家霸道撒泼,常欺负两个妹妹;在外则常出些稀奇古怪的主意和一帮小伙伴搞些恶作剧。惹得乡邻们看到我们就像遇上一群恶犬,要么避之,要么驱赶之。而修理我的责任似乎全由母亲承担,隔三岔五就要被母亲打骂一次。应该是上二年级时,我竟与几个玩伴逃学,偷偷躲到水泥洞里学抽烟。这下单打变成了混合双打。平时少言寡语、一脸憨态的父亲痛下杀手,打得我又是下跪又是起誓方罢手。
应了严是爱宽是害的古语,被父母这次整治后的我虽然还常常刁钻作怪,终究从此守规中矩,认真求学起来,每学期都能领若干奖状回来。父亲就亲自去摘些槐树针,用那粗糙的手将奖状钉在用芦苇柴扎的山墙上,自豪之情写在他满是风霜的脸上。现在想来,这时的他应记忆起他当年读书的情景,欣慰玩劣的儿子终于如他当年好学上进了。
工作后,从教了两年的我进了县政府机关,从县领导身边工作人员逐步走上“有职有权”岗位,父亲从没介绍或带人来找我“办事”。我每次回家或他来看我,他皆用从报纸电视上看到、耳朵听到出事的人和事敲打我:不要吃两天好饭就认不得自己!
和大多数农家人一样,父亲对祖上虔诚敬重。每逢七月十五,冬至和春节,再拮据也要买几个菜,或让母亲包些饺子,向着爷爷的牌位或爷爷奶奶坟墓方向,烧纸磕头祈福。他还有一个求平安的方法,就是每年春节,让母亲用红纸剪出大小不等的葫芦,他用蝇头小楷而且繁体写上“散灾老爷本姓雷,见了葫芦就转回”,不但自家门上贴,还要送给亲戚乡邻。即使几近失明,也要眼睛紧贴小葫芦,颤颤巍巍写几张。
岁月无情。80岁后,病魔缠上了父亲,除了眼花耳聋,脑梗反复发作,还染上了心肺病,肾脏与前列腺也都出现了问题。他用坦然和不歇的劳作与病痛作顽强斗争。从医院一回家或稍有点精气神,就到家前屋后挖地除草。蹲下爬不起来,就拿根拐杖,端个小板凳去。到了风烛残年90岁了,还用钝口的斧头和生锈的錾子劈木柴。真的让人难以置信,这么大岁数,又拖着一身病的他居然劈了几大堆木柴。

图片来自网络
这就是我深植土地、逆来顺受、老实本分、操劳一生的父亲,他用瘦弱的身体和坚强的意志,含辛茹苦撑起一个家,用件件看似平凡实是厚重伟岸的“家风家教”引领子女成长成人。
父亲名蒋福田,生于1930年10月5日(农历八月十四),卒于2022年12月31日(农历腊月初九)。愿老人家在那个世界不要这么辛苦那么负重!
(一)
含辛茹苦九十载,
恩重如山忆满怀。
愿跪床头长尽孝,
亲不待兮阴阳隔。
(二)
坎坷一生磨难多,
日夜劳作稻梁谋。
甘作牛马无怨语,
只求儿女少受苦。
安贫守道笑荣辱,
忠厚善良乡邻睦。
沧桑音容烙心头,
父爱深远思缕缕。
编辑:杨 信
 会员投稿
会员投稿 |
淮安频道
|
淮安频道